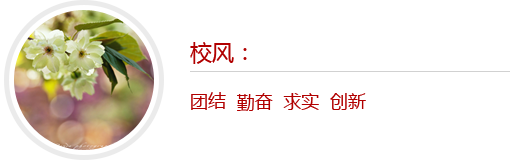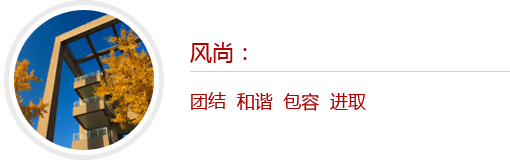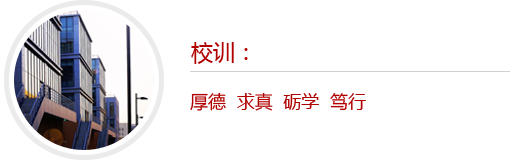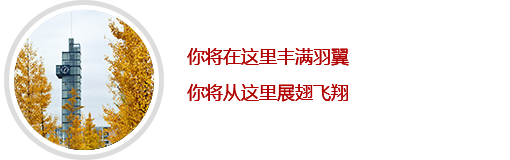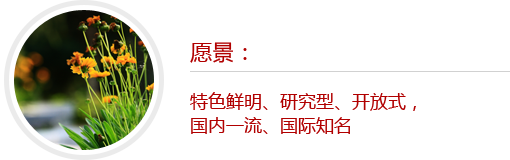2月28日,全國婦聯、中國科協、中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國委員會等宣布,授予10位優秀女性科技工作者第十三屆“中國青年女科學家獎”。年輕的80后美女科學家——西安電子科技大學雷達信號處理重點實驗室教授杜蘭光榮入選。
杜蘭,一位80后溫柔舒雅的女子,但已從事著雷達信號領域最為困難的研究方向之一——雷達目標識別技術10余年。
師出名門,花香自苦寒來
“早在本科畢業設計我就已經開始接觸了雷達目標識別,這個方向是我的導師保錚教授安排我去做的,后來通過一段時間的研究,我逐漸了解到雷達目標識別是一個很小眾的科研方向,研究起來很難,很長一段時間內,在保老師的團隊中沒有老師專門去負責。”杜蘭說。
已耄年的保錚教授是我國雷達研究領域的學術權威,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據了解,雷達目標識技術在上世紀80年代就被美國列為國防關鍵技術之一,是關乎一個國家防御能力的重要技術范疇。同時涉及雷達目標識研究的問題,也一直都是學科中難啃的硬骨頭難題。
因為雷達目標識別是一個交叉方向,除了傳統的雷達系統、信號處理之外,還涉及機器學習和模式識別,要通過回波特性分析目標屬性。而對于虛假或偽裝目標的識別,人們要確定一個基準的門線,以區別判斷真實目標與虛假或偽裝目標。
“碩、博學習期間,我集中研究了高分辨雷達回波特性分析和統計建模。保老師一直很強調物理概念,所以,我們研究在結合雷達回波特性方面是很有特色的,也發表了多篇高水平的國際論文。”杜蘭說。
據悉,杜蘭的博士學位論文曾獲得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獎。但博士僅僅是邁入研究難題領域大門的起步,特別需要具備最新的機器學習和模式識別方面的知識。
“出于這個原因,2007年9月,我前往美國杜克大學進行博士后訪問學習。我所在的Lawrence Carin教授研究小組在有關統計機器學習方面國際上很有名氣,我在該小組做的是基礎的貝葉斯統計機器學習研究。”杜蘭介紹說。
在杜克大學,學校有一項“Safe Ride”的福利,就是學校為了保障學生安全,晚上可以免費送住在附近的學生、博士后回公寓。那時候杜蘭經常工作到凌晨一兩點,反復修改、糾正自己的設想,甚至三四點,獨自一人叫Safe Ride;時間長了,一個白頭發、白胡子的司機都認識她了,經常在回家的路上和她聊天,問關于中國、關于科研工作的問題,也說做科研工作也好辛苦呀。回想起這段小插曲,杜蘭印象很深刻。
國外學習交流進修回國后,歷經十多年攻關,杜蘭帶領研究團隊在高分辨雷達回波特性分析的基礎上,獨創性的提出了高分辨回波統計識別框架,對應了一系列由簡單到復雜的基于統計建模的識別方法。
這種方法相對于傳統識別方法,更適合于雷達目標高分辨回波的特性,在應對噪聲、干擾和在線建庫方面都更具優勢。
此外,為了使雷達目標識別技術滿足實際應用的需求,杜蘭也是最早將貝葉斯統計學習方法應用于雷達目標識別的學者,重點解決了小樣本學習和噪聲穩健兩個關鍵性的工程應用問題。相關成果不僅在雷達目標識別方面受到關注,在貝葉斯方法理論研究、圖像處理、生物信號分析、智能交通管理等其他應用方面的論文中多有被引用參考。
“雷達目標識別不僅僅是理論問題,同時也涉及系統工程問題。”談到團隊項目獲獎情況時杜蘭介紹講。
“我們在國內首次將目標分類方法應用到了型號雷達系統中,實現了雷達目標識別理論方法的具體應用.......”
“一個技術理論方法的實用化是一個不斷試驗、不斷改進的長期過程,可能需要很長時間很多人的努力才能實現。在理論研究時,可能環境的設置都比較理想,但是在工程應用中,實際的系統環境,有限的系統資源和時間分配都與在實驗室不同,利用有限的資源來實現目標識別的功能就需要不斷地去改進和調試,這才是在應用中最大的困難。這個獲獎的項目如果從初期的理論算法研究開始算起,前前后后一共經歷了大概有15年的時間。”杜蘭說。
杜蘭所在科研團隊完成的雷達目標分類技術項目獲得了2015年國家技術發明二等獎,為提升我國現有裝備的信息獲取能力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據了解,當時因項目需要,杜蘭和研究生在一年內需多次去外省荒涼某地處理數據,最長的時候要待近1個月。為了保證學校的教學工作,她只能多次往返西安和外場地,行程最緊的時候一周要往返兩趟某地處理外場數據。
學高為師,傳承西電學風
“談不上成就,只能說取得了一些進展,這要十分感謝保錚老師的指導和引領。保老師教會我最基本的科研方法,首先是物理概念,其次才是數學算法,還有歸納總結的能力以及做科研的嚴謹和仔細。”談到目前已經取得這這些成果,杜蘭十分謙虛地如此而說。
杜蘭認為,對物理慨念的理解很重要!她深有體會。“博士學習期間,保老師通過實際案例的教導經歷使我明白:數學算法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物理概念,只有把牢牢的把握住要解決的物理問題,才能用對、用好數學算法。這也是我們團隊一直在延續堅守的一種研究理念。
談到培養研究生的體會,杜蘭表示:“首先要嚴于律己,以我為表率,高標準、嚴要求,不斷提升自己;其次是對科研能力和嚴謹科研作風的培養。”“延續著保錚老師對我的教導,我十分重視引導學生從物理層面把握新方法、新概念,不用一味地陷入算法和數學推導。”
杜蘭也重視對學生論文的修改,將保錚院士當年一字一個標點修改自己論文的做法用到了她自己學生的身上,幫助學生形成標準、規范的寫作習慣。據悉,她們團隊一直有著堅持讀文章,定期做工作匯報和討論組會的傳統,以培養學生的歸納總結能力,加強學生之間的交流。
“在報考研究生選擇導師時,看到杜老師的介紹,對于如此年輕的老師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感到很震撼,也因此報考了杜老師的研究生。然而上了研究生之后感到更加震撼,因為感覺不管我們多早來實驗室,杜老師都已經坐在實驗室開始工作了。”來自學校電子工程學院的研二學生劉彬說。
“我非常重視專家在評審和答辯時提出的意見和問題,不僅在當時會思考回答,事后我也會反復琢磨,我認為這些專家是在幫助我把握自己的科研方向。而相比于稱號和獎項,這才是最大的收獲。”杜蘭說。
“我感覺科研工作貴在堅持,學習和研究雷達目標識別問題很難!一些同學、朋友和學生也問過我,女生做科研工作是不是太苦了。對我而言,雷達目標識別這個研究方向很重要,而我們現在還有很多問題沒有解決,做的還不夠好。所以,因喜歡這個學科,對于難題我不會放棄,有信心攻克它做出最好的!不覺得有多苦。”杜蘭堅定地說。
從一個西電小女生到今天的中國女青年科學家,杜蘭每一步前行都是迎接挑戰的結果,一個個成績的背后都是學術創新力量的堅持和不懈努力的攀登。
今天杜蘭才進入繼續跋涉“雷達目標識別”領域崇山峻嶺的佳境狀態。
(文/中國科學網·李 直 張行勇)